中国慈善家 · 2025-07-14
中国慈善家 · 2025-07-14

编者按

在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慈善”实践,有着远超这一固定称谓的传播、流行的历史。影响力慈善研究院2025年《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报告的《科学慈善国际扫描报告》章节,深入梳理了全球科学慈善实践的悠久历程,因其内容自成体系且富有洞见,特此分篇呈现。
全章将分上下两辑:上辑《科学慈善:从历史实践到现代奠基》聚焦从古代渊源至19世纪末现代根基的奠定;下辑《20世纪至今的科学慈善》则续写20世纪至今的发展新篇。
以下为上辑《历史溯源:科学慈善的千年脉络与现代奠基》。
科学慈善的发展历史是一段语言、观念、实践变化交织的历史。这三个维度当中,最基础的因素当属实践,正如那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所表达的,实践无时不刻不在变化,而人们的观念与话语经常会滞后于实践。但当观念发生变化时,反过来又会促进实践的发展。
科学慈善溯源
科学慈善最早可以回溯到什么时候?
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需要进入科学史、慈善史两条脉络中去找寻。再加上“科学”、“慈善”二词本身在各个语言中也有其发展演化的历史,这又进一步为溯源增加了难度。 “科学”一词很晚才在中文中出现,即使是在英文中,“科学(science)”一词也只是到了19世纪才逐渐被广泛使用。因此,如果仅仅使用文献检索的方式来思考前述问题可能会受到语言的限制。
英文世界中,“科学慈善(science philanthropy)”一词最早于何时、在何种情况下被首次使用已无从考证。“科学慈善(science philanthropy)”作为一个专门话题、一种共同语言被讨论,很大程度需要归功于2013年成立的科学慈善联盟(Science Philanthropy Alliance)的推广,这是近十年的事。

那么科学(science)一词出现之前有没有科学现象呢?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可能会略有争议,有一部分人可能认为科学本身就是近现代才有的现象——这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科学”这一概念。绝大多数的科学史研究者对“科学”持相对宽泛的理解,主张其起源(或精神源头)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时期,与英文“科学(science)”一词的出现并无直接关系。在该词出现之前早就有科学现象,只不过被冠以其它名称。例如,早期科学家使用“哲学”或“自然哲学”来称呼其研究对象,例如牛顿创立牛顿力学体系的著作名为《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进化论伟大先驱拉马克的代表作是《动物哲学》(1809)。当然,科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态和特征,在科学史上会有古代科学、近代科学、现代科学的区分。
慈善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对慈善持相对宽泛的理解,可以认为慈善与交往、交易等行为一样,是人类基础行为的类别之一,与人类自身历史一样久远。与科学史可以划出不同时期一样,慈善也可以分为古代慈善、近代慈善、现代慈善。
如果从人类基础行为与活动的角度来理解科学、慈善,那么我们对科学慈善源头的回溯就可以突破语词的限制,也不完全受制于文献记载,而是更多地从原理角度来思考。我们知道,科学作为人类主要出于求真目的而开展的、系统化的认知活动,与以满足个人生存所需和创造利润为目的生产活动有显著区别。科学活动要想能收获成果,需要投入的时间周期相对较长,不确定性更高,并且不一定会获得经济上的回报。能够既从事生产又开展系统化求真求知活动的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
通常情况下,系统化的求知活动都难以仅凭自给自足的方式获得即时回报,产生类似于“生产-消费-再生产”的自我造血循环,而需要来自其它活动或外部力量的支持。而支持的提供可以有两种来源,要么来源于公共资源,要么来源于私人资源。而来源于私人资源的,提供资源者又可能出于两种类型的目的,要么提供资源的同时希望获得经济回报,要么提供资源但不追求经济回报。私人为科学发展提供资源支持,同时又不追求经济回报的行为,就可以归为科学慈善。从原理角度思考,这类行为应该有很长时间的历史。
上述判断可以从史料和文献当中获得支持。可以说,自科学精神自古希腊发源以来,整部人类文明史中的各个时期,都可以找到科学慈善的身影,只不过有时见于科学史,有时又在慈善史中出现。从18世纪的瑞典皇室支持设立瑞典皇家科学院,到17世纪的英国皇室支持设立英国皇家学会,再到15世纪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对伽利略研究天文学的资助,乃至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对亚里士多德建立吕克昂学院的支持,都可以归为科学慈善。
当代研究者关注的“科学慈善”
由于“科学慈善(science philanthropy)”一词的早期使用历史相当模糊,因此当英文世界的当代研究者需要界定一个叙述起点时,很多研究者特别是美国研究者往往会提到《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Bush,1945)的发表。

这一发布于1945年的知名报告是美国科技政策领域的开山之作,在世界科技政策史上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科学发展的格局,对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起到了推动作用,无疑是里程碑式事件。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沿用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此外,该报告还旗帜鲜明地提出政府应该为科学提供资金支持,并直接促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设立。

虽然《科学,无尽的前沿》所呼吁的主要是政府资源对科学的投入,但当科学发展背后的“支持”被关注时,慈善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科学慈善”的早期倡导者对该话题的关注主要是从资源视角出发的。不同时期科学发展的需求、科技竞争的态势和国家对科学的投入都是不断变化的,当科学界的资源渴求与政府的资源投入差距变大时,“科学慈善”的呼声也会提高。
《慈善与科技未来(Philanthropy and the Fu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chelson,2020)一书中回顾了权威期刊《科学》(Science)上先后刊出的包含典型科学慈善倡导呼声的两篇社论及其产生背景。第一篇社论发表于1997年,当时的美国政府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哈勃太空望远镜、纳米技术研究等多个基础科学领域,投入了大量的政府资源。然而,这篇社论具有先见之明,指出要让科学事业继续前进并在未来蓬勃发展,单靠政府资源是不够的。社论作者写道,“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过渡,为美国慈善事业提供了一个回顾其历史,并重申其对科学的承诺的机会”(Fitzpatrick & Bruer,1997)。第二篇社论与第一篇社论相隔近20年。2016年,《科学》杂志上再次发表了呼吁推动科学慈善发展的社论。作者呼吁将更多慈善资源用于基础研究,以增加和补充公共部门提供的资金。这篇社论指出,“为解决一些最大的社会问题,我们不仅需要专注于基础科学研究,还需要足够的资源和新方法”。作者继续强调,慈善捐赠有可能激发新的研究方向并承担政府资助可能难以承担的风险(Baltimore,2016)。
通过这样的回顾,《慈善与科技未来》一书的作者认为,人类需要重新关注(renewing attention on)科学与慈善的互动,关注科学慈善的第二波浪潮已将到来。与第一波浪潮主要强调慈善部门的资源供给能力不同,第二波浪潮除了延续前述资源视角之外,还试图突出科学慈善的一些比较优势,比如慈善对于科学研究方向设定的作用等。
《慈善与科技未来》一书是科学慈善研究领域的最新专著,作者对研究材料的处理和剪裁很有代表性。与书中的处理类似,“科学慈善”的关注与倡导者在对相关历史做回顾时,通常会回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这一百年,以及我们刚刚走过的、21世纪前二十年是被当代研究者谈论最多的时期。回顾过往,20世纪的确是科学慈善发展的主要世纪。进入21世纪后,科学慈善更是迎来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变化,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尽管现代科学慈善的主要发展出现在20世纪,但19世纪也被视为现代科学慈善的源头。
19世纪末的科学慈善里程碑事件
19世纪末科学慈善的里程碑事件包含一些重要机构(大学、基金会)的成立和一些重要观点的提出。这一时期是现代大学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现代科学”“现代慈善”等理念的奠基、初创时期。
1887年 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基金(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Endowment)设立

该基金由慈善家霍普金斯遗赠700万美元设立,旨在支持医学研究与高等教育,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慈善捐赠。这笔资金推动了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的诞生,对全球高等教育与科学资助体系影响深远。
1889年 美国 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发表《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通过《财富的福音》主张,富豪有责任在有生之年回馈社会。这一作品在当时就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并且其影响力还绵延至后世,被很多人视作开启现代慈善时代的经典著作。在《财富的福音》发表之后的几十年中,卡内基先后设立了卡内基基金会、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等众多慈善与科教机构,将大量财富投入到了支持公共教育和科学的方向上。
1891年 美国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成立

该大学由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及其妻子简·斯坦福(Jane Stanford)捐资创办,初衷是纪念他们的早逝子女。斯坦福大学后来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一,在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等领域推动科学慈善的发展。
1895年 瑞典 诺贝尔基金会(Nobel Foundation)成立

该基金会据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的遗嘱设立,致力于奖励为科学、文学和和平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士。诺贝尔奖后来成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奖励之一,极大推动了基础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和科学传播。
19世纪末对于现代科学与现代学科知识生产体系而言都是初创时期。大学虽然在中世纪就已出现,但根据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研究,现代意义上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自19世纪初德国洪堡大学的创立才正式开启,到了19世纪末,随着大学的增多,现代大学才逐渐形成一种体制。

19世纪是西方近代慈善向现代慈善过渡的时期。在19世纪早期,慈善主要由宗教主导,教会及教会发起的医院、孤儿院和救济组织是主要的慈善活动载体。19世纪中期,现代慈善理念和慈善信托、基金会等现代慈善机制逐渐出现,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第一代富豪慈善开始兴起,现代慈善已初具规模。
《财富的福音》的发表,以及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富豪将事业的重心转向慈善都是这一时期内的重要事件。被认为是现代基金会先驱的重要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在迈过20世纪的门槛后才成立,但现代慈善规模化发展的种子早在19世纪就已种下。
在这一时期,科学与慈善有丰富的互动,二者相互影响,各自为对方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助力。私人捐赠推动了研究型大学的设立和扩张,促成了现代大学体制的形成;反过来,科学的理念也推动了传统慈善向规模化、机构化运作的现代慈善发展。
此外,最早的“科学公益(scientific philanthropy)”倡议也出现这一时期,该倡议旨在倡导“科学地做慈善”而不是“通过慈善支持科学发展”,但受早期科学公益倡议激励而产生的行动却常常符合科学慈善的界定。正是因为上述表现,我们才说,19世纪末,可视为现代科学慈善的奠基阶段。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2025-0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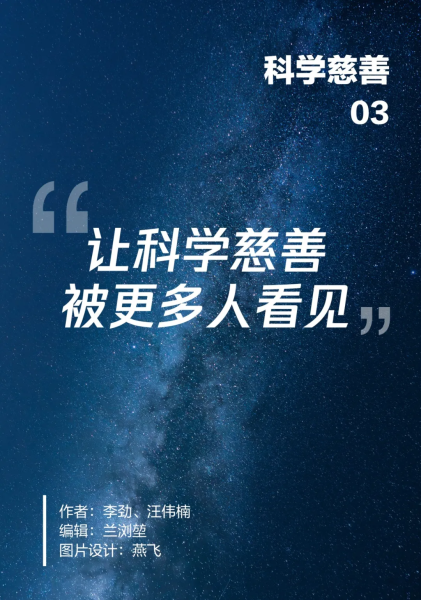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2025-0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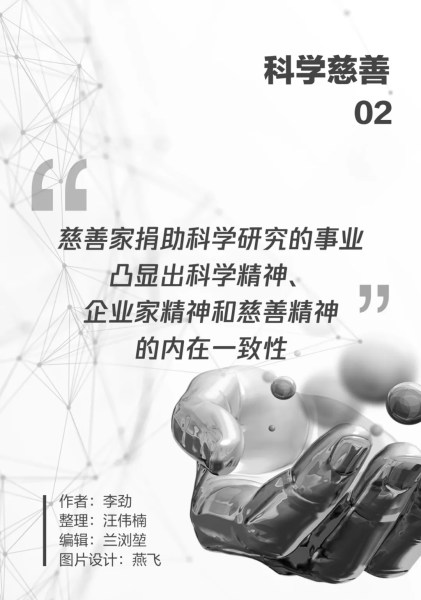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2025-0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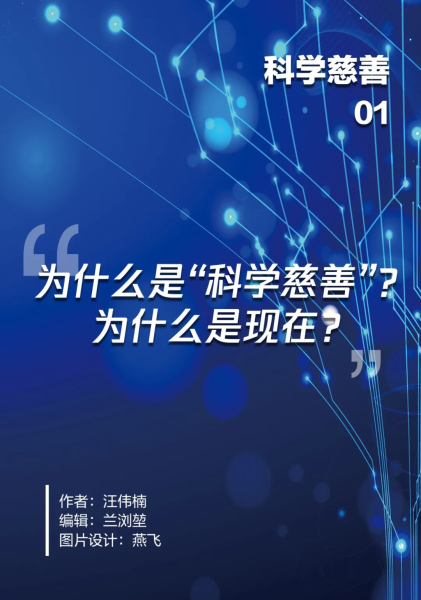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2025-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