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 · 2025-09-18
中国慈善家 · 2025-09-18

编者按
世界范围内,科学慈善是推动罕见病科研与药物研发的关键。中国首个由患者社群深度驱动的罕见病科研资助项目——由浙江瑞鸥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金石计划”项目,正在探索一条创新路径。“金石计划”由罕见病患者家庭出资,基金会专业管理,联合科学家,共同瞄准罕见且无药可医的疾病,加速个性化治疗探索。它填补了市场失灵的空白,其创新模式与本土化实践,为科学慈善提供了“中国样本”。上海市乐知一心基金会慧眼识珠,率先对金石计划项目的专业化管理运作、影响力传播进行了资助。
本期科学慈善专栏访问了瑞鸥基金会项目总监张文君、乐知一心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廉旭,从执行方与资助方的双重视角,力图展现金石计划项目的全貌。
以下是访问的主要内容。
创新模式:患者需求驱动的科研资助闭环
汪伟楠:首先请文君再详细介绍一下金石计划,特别是这一项目与众不同的特点,这种模式在公益领域并不多见,大家可能需要更多信息来帮助理解。
张文君:金石计划是瑞鸥基金会由患者社群定向捐赠形成的一个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的起点,来源于一些无药可医的罕见病患者未被满足的真实需求。患者家庭,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捐赠方。瑞鸥基金会,是项目的管理方。我们要去联合包括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以及围绕科研服务在内的多方主体一起合作、整合资源,共同去推动创新的疗法和关键技术在推动人类一些复杂疾病研究中的应用,也是对罕见病个性化治疗的探索。
这个项目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科研价值高。因为我们现在关注的方向聚焦在特别罕见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尚无治疗和解决方案的疾病。研究这些罕见而复杂的疾病,对推动全人类的健康发展、对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二是公益性强。我们资助不以商业注册为唯一目的的临床前科学研究,希望推动研究能够走到临床应用,尽管这些临床的应用和成果未必都有商业开发的价值,但这部分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又缺乏政府资金或者商业资金推动的部分,我们认为恰恰是公益慈善机构要去重点推动的。
三是模式新。首先,运作模式新。在推动整个研究全程专业高效的进程管理中,基金会扮演着资源整合、成本控制和过程把控的关键角色。我们希望用尽量低的资金成本、尽量短的时间,让有限的捐赠发挥最大优势,去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力。其次,募资模式新。我们立项的项目资助款,大部分来源于患者及其家庭的定向捐赠。因为罕见病的患者群体,对推动自身所患疾病的科学研究有着最强大的驱动力。除了这些定向捐赠之外,基金会还会为每个项目再配捐部分资金和资源,确保项目能够顺利开展。关于我们的运作模式,这里有一张图,可以直观展示。

另外,金石计划的项目周期和实施流程也漫长而复杂。通常我们都是先收到患者及其家属的定向捐赠需求,希望通过向瑞鸥基金会捐赠一笔资金,用于支持自己或者家属所患疾病的科学研究。在收到需求后,我们会先做可行性评估,评估捐赠者是否理解捐赠的行为,是否接受科研可能失败的风险,同时,也初步评估这个疾病是否在中国有相应的研究团队。如果初步评估可行,那我们会接受这笔捐赠,正式立项。立项后,我们会成立这个项目的专家顾问小组,并邀请研究团队来设计研究方案,进入到专家评审环节。如果这个项目有多个团队在研究,我们也会公开招募研究者,进入到招标和评审的流程。我们的项目专家小组,由研究者的大小同行组成,他们不仅为项目提供评审,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一些专业性的建议。
在确定了承接这个项目的研究者之后,接下来会进行到项目拨款、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的不同阶段,顺利的话,最终会有研究成果的发表。这就是我们“金石计划”科研项目的资助全流程。
这个过程中,患者家庭作为捐赠方捐赠到基金会,基金会作为资助方,资助给每项研究选定的主要研究者。主要研究者有些来自科研机构,也有些来自医院,但多数都是由来自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的研究者与来自医院的临床研究者共同合作。流程的示意图如下,供大家参考。

资助逻辑:赋能专业价值与影响力
汪伟楠:瑞鸥基金会在金石计划的整个流程中扮演多个角色,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作为研究者的资助方。乐知一心相对于瑞鸥来说又是资助方,我想请问,乐知一心在资助“什么”?又是如何考虑的?
廉旭:我先回答我们为什么资助,然后讲一下我们资助什么。首先,结合文君的介绍和刚才展示的两张图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实瑞鸥基金会、金石计划项目发挥的作用远远不能用“资方”这两个字来概括,它的角色和功能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它面向罕见病创新科研的研究者,有筹资的功能。这里的筹资,还不是单纯的国自科、国社科这样的国家资助,或者企业、投资者的商业支持,而是能达到一些社会化的资金,是一个支持性的筹资。另一方面,它也面向财富阶层,只不过稍微有点特殊,是受罕见病影响的高净值家庭,在做劝募工作,就是鼓励大家,为了系统性地帮助身边的患者、自己的亲人,你可以选择支持科研。都是和资金打交道,一方面看是筹资,另一方面看是劝募。并且它在整个过程中,会创立议题、设计路径,包括会创造性地找到一些合适的沟通方式。
虽然类似的模式在国际上不是首创,但把这个事情在中国跑通,是从零到一的突破,这很不容易,需要大量的本土化经验。所以从多个角度上看,这并不是一个单纯地“选项目资助”的活动,金石计划在多个生态位承担了多重角色,是非常有专业性的。我们首先是看到了金石计划的闪光点,其次我们觉得金石计划能带来突破,并且这个突破是非商业化目的驱动,带有很强的社会愿景。
那么我们到底资助什么?说起来,我们一年30万的资金支持,与金石计划调动的资金量、做的事情相比是很少的。金石计划资助的研究,每一项的综合成本可能是百万量级,200万到500万之间,如果是六、七条研究管线同时在跑,合起来可能就是千万量级。
面对几千万量级的盘子,30万的资助能解决什么?我们是这么考虑的:三分之二用于金石计划本身的影响力。金石计划要劝募,要整合资源,需要把故事讲好、道理和模式解释清楚,要做传播,让更多的人认可这个路径——这就是影响力的打造,这部分钱能用好,是很值的。剩下的三分之一作为项目人员经费和综合管理费。我们用偏向于非限定的钱,支持金石计划的项目人员做好运营、管理,做好专业的事,这也是对他们专业的认可。
最后,对于乐知一心来说,我们做资助的底层逻辑就是支持中国健康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MVP)的落地。从这个角度看,长远来说,支持金石计划是效率很高、杠杆效应很强的。我们也希望借着对金石计划的资助,让整个转化医学生态活跃起来,增加患者、资助者、公益行动者在其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撬动增量慈善资金投入到科学研究来,致力于对卡点问题的突破。
本土突破:构建患者驱动科研的生态价值
汪伟楠: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金石计划有哪些创新?为什么要走“患者驱动”的模式?这是金石计划独有的创新,还是国际上罕见病相关的研究领域常见做法?
张文君:对于瑞鸥基金会来说,“金石计划”的项目模式,并不是我们独创的。在设立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吸取了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是有例可循的。慈善资金去推动罕见病的科学研究,美国有很多经验,比如囊性纤维化、亨廷顿病和杜氏肌营养不良等。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囊性纤维化基金会(Cystic Fibrosis Foundation, CFF)。
这家基金会成立于1955年,它在囊性纤维化这个疾病的研究上,从1989年资助科学家找到致病基因,到2019年一款突破性疗法获批上市,近30年间,基金会为囊性纤维化的药物研发一共投入数亿美金,在2014年将药物权益以33亿美金售出,向我们展示了科学慈善的可行性。这笔巨大的收益,支持了这家基金会目前每年持续投入超过1.6亿美金继续用于科研资助,每年资助超过300个科研项目。
但这样的模式,也并不是瑞鸥基金会可以完全模仿的。比如,根据政策法规,美国的基金会是可以直接向研发企业进行风险投资,但在中国现阶段还行不通。所以想把这个模式跑通,我们必须要结合本地化的经验。
另外,罕见病患者驱动的科研资助,其实并不罕见。因为常见疾病患病人数庞大,市场规模可见,因此对药企和资本有极大的吸引力来推动药物研发。而罕见病面临着患者人数少、科研难度大、投入大风险高、未来支付困难的这些挑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调节失灵。要知道中国有大约2000万的罕见病患者,受到影响的家庭和人数可想而知。
面对95%的罕见病病种无药可医的现实,不管是中国的患者,还是其他国家的患者,他们都身陷困境。尤其是那些超罕见的疾病,全球已知的患者可能只有一百人的这种疾病,谁有动力去推动疾病的研究,患者只能无望等待吗?罕见病患者推动科研资助,是我们尝试探索的一条很重要的路径。
说完这些实际背景,再来理解一下金石计划的创新:一,模式落地的创新。国外类似的做法早就有,国内患者的捐赠意愿也一直就有,但难就难在落地。想要落地,一定熟悉环境,要想办法把落地的障碍解决,比如说,我们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包括和律所合作,做到合规,把控风险,让项目合规合法地开展。二,推动科学本身创新。金石计划支持的一些研究,虽然是从单一病种出发,但它蕴含推动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可能远远超出单一的病种,而是对全人类有益,例如一些基因疗法关键技术的探索。三,推动医疗模式创新。金石计划也有助于在中国跑通“个性化治疗”的可能性。
廉旭:我补充一点,这里有一个政策背景,我们国家大力支持“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nvestigator Initiated Trials,简称IIT)”,这是国内的政策创新,是中国特色,不是全球都有的。患者驱动的金石计划,和IIT可以很好地结合,它最大的特点是快,而很多罕见病无药可医,真的是分秒必争。另外中国罕见病患者基数大,需求大,所以我们国家是既有好的环境,又有最刚性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金石计划可以说是站在了非常重要的点上,在支持创新方面很有潜力。
另外,我还想提一点,关于金石计划的意义,或许对我们思考“科学慈善”能提供一些启发。我理解金石计划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尝试与商业共舞,通过撬动健康的商业决定因素(Commer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DH)来实现对与社会需求的有机对接,推动罕见病领域的科学创新,实现健康公平。当我们要面对药物研发的“死亡谷”、面对各种政策不足或政策限制、面对患者付费能力不足的现状,但我们又想真正去回应患者的需求时,我们就需要走在商业的前面、走在政策的前面,超越传统“产学研”的小圈子,去试着解这道题,哪怕现在无解,也为未来解题的可行性进行充分的论证。这一步可能是慈善力量最擅长,也是最有可能形成突破的。
汪伟楠:这涉及到“慈善”观的问题,我感觉在你这里理解的“慈善”,并不是与“商业”相对、相矛盾的概念,而是一个更前瞻、更超越的概念,是可以与商业共舞的——为理解“科学慈善”,提供了很好的注脚。感谢!
作者|汪伟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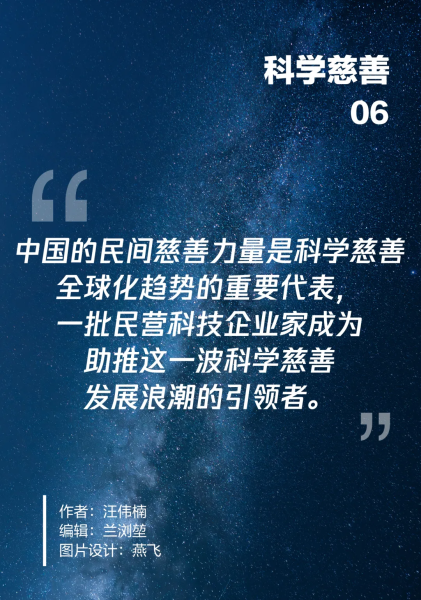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2025-09-18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2025-09-18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2025-09-18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2025-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