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 · 2025-09-18
中国慈善家 · 2025-09-18

编者按
在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慈善”实践,有着远超这一固定称谓的传播、流行的历史。影响力慈善研究院2025年《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报告的《科学慈善国际扫描报告》章节,深入梳理了全球科学慈善实践的悠久历程,因其内容自成体系且富有洞见,特此分篇呈现。
全章将分上下两辑:上辑《科学慈善:从历史实践到现代奠基》聚焦从古代渊源至19世纪末现代根基的奠定;下辑《20世纪至今的科学慈善》则续写20世纪至今的发展新篇。
以下为下辑《20世纪至今的科学慈善》。

20世纪初期,一批今天在科学慈善领域广为人知、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陆续出现并活跃至今,其中许多机构对当今世界人类知识版图的形成有很深的影响。
20世纪不仅是全球知识生产进一步体系化、建制化的发展时期,也是慈善从形式到规模都迎来重大发展的时期。正是在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慈善开始以一个与政府、市场并立且相对独立的姿态出现,慈善的主流形式也从传统的私人短期行为为主走向了现代慈善所追求的,以项目、组织的形式做出战略安排、展开管理运作为主。慈善在整体上进入了规模化、体系化发展的时期,相关制度也相应发展。
20世纪的科学慈善,在美国成为全球科技中心,知识生产与慈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背景下发展。
20世纪的科学慈善里程碑事件
20世纪科学慈善里程碑事件类型丰富,既包括重要机构的成立、重要观点的提出,也包括一些重要政策的出台。受限于篇幅,这里仅仅举出了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1913年 美国 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成立
该基金会由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创立,旨在推动全球健康、教育、农业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基金会在全球公共卫生和医学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资助建立了一批世界顶尖的研究机构。
1936年 英国 威康信托(Wellcome Trust)成立

该机构由制药企业家亨利·威康(Sir Henry Wellcome)遗产资助,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之一,支持从基础医学到流行病学的广泛研究。
1953年 美国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HHMI)成立

该研究所由航空与医疗器械企业家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创办,专注于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为全球顶尖科学家提供长期资助,推动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等研究的发展。
1980年、1983年 美国 《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孤儿药法案(Orphan Drug Act)先后颁布
拜杜法案允许大学、非营利组织和小型企业对其在联邦资助下取得的成果申请专利,并允许其从专利的商业化运作中收益。这提高了私人资本(如基金会、企业)资助科研项目的积极性,提高了科技成果的商业转化率,并且大大推动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科学等科学领域的发展。
孤儿药法案鼓励罕见病研究、孤儿药开发的慈善资助。该法案通过后,大量企业和私人基金会(如盖茨基金会、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积极资助孤儿药开发,推动了全球罕见病治疗、基因治疗的进步。
1998年 英国 英国国家捐赠科学、技术和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NESTA)成立

NESTA由英国政府创立,旨在通过资助和支持创新项目,推动英国在科学、技术和艺术领域的发展。其初始资金来源于国家彩票基金,虽然其董事会由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任命,但NESTA设立时即为非政府机构,并在2012年注册为一个独立的慈善机构。目前NESTA专注于通过支持创新来解决社会问题,是英国科学慈善最重要的资助方之一。
科学慈善建制化、规模化发展的百年
20世纪的科学慈善,不仅资助的主流形式与以往不同,其规模和机制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首先,20世纪上半叶,现代基金会模式逐渐确立。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相继成立,并且还在20世纪中期将资助的重点逐渐从创立初期的较窄范围拓展到了系统性、长期性的科学研究、教育支持等方向。这些基金会通过捐赠研究机构、设立奖学金、支持跨国科学合作等诸多方式,推动了全球科学体系的构建。
随着知识生产的专业化不断深化,专业、学科开始成为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建制力量,影响着智力、资金等资源的分配。而慈善力量推动学科建设,或是促成已有学科发展出新的研究方向乃至全新学科形成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该时期科学慈善在科学发展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例如,计算机科学发展方面,洛克菲勒基金会直接促成了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这一专门研究领域的形成。事实上,“人工智能”一词被首次作为专门术语使用,正是出现在该领域开创者数学家约翰麦卡锡1956年提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学术会议资助申请书中。
其次,政府与私人慈善的合作模式在20世纪逐步成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英国威康信托(Wellcome Trust)等机构在20世纪后期成为政府与慈善资本共同资助科学研究的典型案例。政府主动颁布激励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基金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加速了科学技术的应用转化。
20世纪后期,在科学研究领域,不仅跨部门合作增多,跨国合作也开始出现并迅速增多。随着科学研究复杂程度的增加,国际科研合作逐渐成为常态。例如,受多国政府共同资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的。虽然在20世纪,同时具备跨国、跨部门这两个特征的大型科研项目十分罕见,但国际科研合作、跨部门联合资助的分别发展,为21世纪科学慈善的进一步演进奠定了基础。总体来看,20世纪是科学慈善建制化、规模化的关键阶段。
21世纪的科学慈善里程碑事件
21世纪的科学慈善在全球化、技术创新、跨学科合作的背景下,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趋势。相比20世纪,科学慈善在这一时期更加注重全球协作、科技驱动,并且涌现出一批新的科技企业家投身科学资助。
到目前为止,21世纪才走完了四分之一左右,但其间已涌现出了众多里程碑事件。在这一时期,20世纪就已出现的跨部门、跨国合作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2000年 美国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成立。

该基金会由比尔·盖茨(Bill Gates)及其妻子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创立,主要支持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控、生物医学研究,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之一,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
2012年 全球 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设立。

该奖项由俄罗斯企业家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联合科技界领袖发起,旨在奖励生命科学、基础物理学、数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现被誉为“科学界的奥斯卡”。这一全球科学界重磅奖项的设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我国慈善家深度参与。马云夫妇受尤里·米尔纳邀请,是该奖项的联合发起人。马化腾自2017年起,加入了该奖项的捐赠人行列。
2013年 美国 科学慈善联盟(Science Philanthropy Alliance, SPA)成立。

该联盟由多个大型慈善机构(如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斯隆基金会)共同发起,以推动科学慈善的发展为目标,致力于提升私人资金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并促进政府、学术界、私人捐赠者的合作。
2016年 美国 陈·扎克伯格科学计划(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CZI)设立。

该组织由脸书(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及其妻子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设立,致力于在21世纪消除所有人类疾病。该组织的投资领域包括生物医学研究、精准医疗以及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等方向。
2020年 全球 COVID-19大流行促进全球科学慈善合作。
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多个慈善机构(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威康信托、盖茨基金会)紧急资助COVID-19疫苗、治疗方案、流行病学及公共卫生研究,这一过程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慈善合作。
21世纪的科学慈善看中国
进入21世纪,科学慈善领域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不断出现,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第一,科学慈善的国际化趋势愈发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和科学资助机构倾向于资助跨国研究合作,推动全球范围内科学研究的共享和知识传播。
其次,科技企业家成为科学慈善的重要推动力量,科技驱动的科学慈善影响力日益扩大。以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马化腾、马云、雷军、陈天桥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慈善家,通过设立基金会或专项计划,支持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众多前沿领域的研究,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利用自身或所在企业拥有的技术资源推动科学慈善发展。
第三,科学慈善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在抗击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领域,慈善机构与国际组织与来自不同国家的政府、企业或个人紧密合作,共同推进相关科学研究及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中国的民间慈善力量是科学慈善全球化趋势的重要代表,一批民营科技企业家成为助推这一波科学慈善发展浪潮的引领者。2012年“科学突破奖”的设立就出现了中国慈善家的身影,这也是为数不多的由国人参与发起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巨奖之一。仅仅几年之后,与“突破奖”的创设过程类似,国内一群崇尚科学、热心公益的科学家、企业家在2015年共同创立“未来论坛”,并于2016年创设了 “未来科学大奖”,奖励在中国内地(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工作并做出具国际影响力的原创科研的科学家。从突破奖到未来科学大奖再到后来的科学探索奖,中国慈善家设奖支持科研的势头逐渐兴起。
不仅如此,《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报告的案例部分显示,除了“奖励”这种模式之外,中国慈善力量在设立科研基金、资助科研项目、成立科研机构、支持科学社群、推动科学普及等科学慈善的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国自己的“科学慈善”范式正在形成。
在专栏的后续几期中,我们将陆续分享这些典型案例,敬请期待。
作者|汪伟楠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2025-09-18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2025-09-18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2025-0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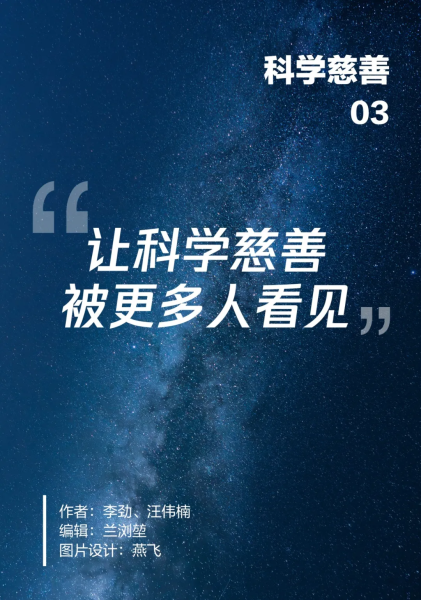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2025-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