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 · 2022-08-22
中国慈善家 · 2022-08-22

花木惠姐团。图/受访者提供
本刊记者/龚怡洁
在上海浦东新区,有一条花木街道。听上去是一条街的地界,实际上是比黄浦区还要大的一片地方。街道下设6个社区,包括52个居委会、168个小区,常住人口达24.9万人。街道如其名,郁郁葱葱,花与木紧紧拥簇,相互支撑。
上半年,在被疫情攫住的上海,“团长”成了一个高频词汇。居委会等基层管理单位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居民们自发组织团购、疏通物流,单元、楼栋、小区,似乎已经沉寂的生活单位突然回到视野中心,疫情中的守望相助让大家“重新发现了社区”。
这其中,花木的故事还有些不一样。给街道上近25万人保供的工作,是由居民、妇联、社工机构加上居委会与企业支持共同完成的,没有变成哪方一意孤行负重前行的独角戏。
但它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故事。在最危急的时刻,搭建一个关乎民生、商业和财政的临时合作网络,必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其中的很多情节是需要十足勇敢和坚定才能写就的。这得益于花木日常的建设与积累,覆盖社区的大网才得以及时撑起来。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五社联动”政策,强调搭建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在过去的三个月,花木的行动也许就是一种应和。
今年的盛夏,《中国慈善家》访问了刚刚迈出疫情阴霾的花木街道,试图为这个珍贵的基层故事留下一些纪录。它的故事围绕着区块与街巷展开,脉络交织,在疫情的静默中也竟流动了起来。
一次联动尝试
庄文菁曾经是一家地产公司的项目经理,有孩子后辞了工作。不过她并非刻板印象中那种囿于家务事的全职妈妈。她在社区创办了一个“联洋妈妈俱乐部”,平日里在公众号上更新食谱、组织亲子活动,调动妈妈们参与社区治理。因为在社区的活跃,庄文菁被推选为花木妇联的执委之一,她还是孩子学校家委会的成员。
3月16日开始,上海进行多轮网格化筛查,小区封控开始收紧,菜市场逐渐关停。庄文菁向《中国慈善家》回忆,那时候明显感觉到了情况和往常不一样。以往多种外卖平台上,新鲜的菜最多一小时就能送到,但3月中旬到月底,盒马、叮咚等平台的运力渐渐不够用,后来门店直接关停了。
被按下暂停键的,还有李碧波铆足了劲的“她创”计划。李碧波是浦东花木街道妇联主席。今年3月8日妇女节那天,街道妇联原本准备组织一场大会,会上将正式启动“花木她创基地”,搭建资源平台,扶持社区内女性创新创业。但就在3月7日,上海出现疫情,李碧波和街道其他人一样被迫居家隔离,会议也被紧急叫停。
李碧波形容自己是一个“不能停下来”的人。说这话的时候,她也显得风风火火,笑得很开,语速很快。来妇联的近两年时间里,她已经盯着儿童友好、家庭文明,做起来了一些项目。眼下“她创”的制度框架都准备好,突然被疫情踩下刹车的感觉让她有点无所适从。
窝在家里,但她仍然注意到了两件事:一个是街道里的商家经营状况受疫情影响变差,另一个是居民有很多需求亟需被填补。“当时居民对居委会有些意见。”她向《中国慈善家》回忆,“我替居委会发声了,因为我是知道居委会有多不容易的。但是我看到居民提到的点,的确有一些正当诉求,是没有被很好地服务的。”
顺着先前被打断的思路,李碧波觉得,妇女力量是眼下一个可以借助的支点。3月19日夜里12点,她敲出一份策划初稿来,内容是搭建一个惠民惠企爱心服务资源平台,群众可以直接发布需求,社区内的企业店铺在上面提供商品,直接供给居民。计划推出后,妇联在社区里发布了志愿者招募令。
3月23日,买菜难的问题已经开始严重了起来,浦东妇联下发了一份农业合作社的联系方式名单,“2000份起送”,上面写着。李碧波突然想,这2000份需求,谁来把它们攒起来?先前想要做的那个平台,似乎刚好能契合这个需求。
那天下午,庄文菁接到了李碧波的一通电话,街道妇联拜托她做个调研,调查网格化筛查期间街道居民买菜的缺口。庄文菁马上应承下来,把问卷发在学校和小区群里。仅一个半小时,问卷就收回来近3000份,数据清晰集中:96%的居民表示有买菜难的问题,而且需要社区出面组织团购。
惠姐志愿者们在小区门口卸货,地上码着一排蔬菜包。图/受访者提供
妇联、社工、妈妈们组成的团队用了两个小时,出了一份分析报告反馈给街道政府。第二天庄文菁再次接到妇联的电话,这次是问她,能不能作为负责人来组织团购?
“我说可以,之前我也做过快团团之类的团购,有些经验。在小区里做的话,我去问了问家委会其他的一些家长,结果大家都挺愿意的。大家平时都很热心,但也没有做过什么团购、群接龙之类的。我跟他们说的时候,真的就是一腔热情,就做起来了。”庄文菁告诉《中国慈善家》。
团队最终给志愿者们定下了“花木惠姐”这个名字——住在花木街道的贤惠女性们。第一团开在庄文菁所居住的联洋社区,3月24日上线,是蛋、米、蔬菜、肉的“山姆超市”套餐。团队开了100单试水,结果很快就卖掉了80份。到了第二天,志愿者大胆地把团购扩大到1000份,当晚就售出了800多单。那时候花木居民已经吃不上菜,惠姐的出现,成了及时雨。
化解风险
想要惠姐覆盖花木的168个小区来解决街道的买菜问题,团队需要落实两件事:一是稳定的供应商和货品,二是充足且可靠的志愿者。
最初,街道的招商中心推荐来了一个供应商,后来网上公布了多家保供单位的电话,团队就开始一个个打电话。也有上海由由集团等公司主动找到花木惠姐,表示可以和街道合作团购。
志愿者则是一直在各个小区招募,从最开始的60人,一直到疫情后期的上千人。每个小区都找了一位负责的团长,以小区为单位各自团购分发。庄文菁回忆,起步时大家卖菜越来越上手,但是第一次分菜却着实累了一把。联洋社区十几个小区,每个门都在不同的路上,联洋花园、仁恒河滨城都有三期,把送菜的司机绕得晕头转向。卸完最后一个小区,已经过了晚上十点。志愿者们还要通知居民们领菜,把没认领的菜一一放在对应的快递架子上。
疫情期间,居民基本是出不了小区的,同时运货车也很难每天开进小区。惠姐把整个团购链条分割成了几段:能征用到有通行证车子的负责去考察供货商,供货商找车把菜分别送到各小区大门处,该小区的志愿者到门口接菜,只要不是封控的楼,会挨个分发到家门口。
最忙的时候,庄文菁所在的联洋社区一口气订购了2000多袋面粉,15个小区平均下来,每个小区也有上百袋要扛要发。庄文菁觉得数据统计是她们面临的一大难题,“每次上千个单量,要给司机每个投放点的数量,虽然后台可以导出数据,但是整理起来还是要费些工夫。”
花木各个社区和小区都开了惠姐团,后来团长们就要求居民,只能在自己小区购买,这样方便各小区负责人导数据;另外,惠姐团里一位在外企工作的姑娘,设计了一份可在线填写的腾讯文档保供单,负责人团购结束后可自行填写后台数据,自动生成出货单给供应商。花木街道小区多,道路也比较复杂。为了提高送菜效率,志愿者们还做了一份送菜路线图,提前发给司机参考。
5月20日,花木惠姐与妇联团购了一批即将滞销的鲜花至街道,小志愿者们在帮忙卸货。图/受访者提供
忙到半夜成为了常态。李碧波回忆,那段时间她基本是早六点起晚三点睡,单子物流出了问题的,她自己跑腿一个一个小区去送。庄文菁则说,志愿者群里明确了做表、对接物流等分工后,大家就随时交流轮班,经常凌晨一两点起来接货。
为了能让惠姐的工作更专业,也为了能激励志愿者们,妇联请来了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做指导。乐群成立于2003年2月,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承担了花木街道家庭中心和儿童服务中心的运营工作,对街道情况非常熟悉。殷茹媛是这个5人社工小组的带头人,她告诉《中国慈善家》,乐群主要负责帮助搭建惠姐的框架体系、培训志愿者,并帮助志愿者们注册身份、记录时长。计划的初期,乐群就出了一本工作手册供大家参考,这也是后来志愿者们面对问题能快速找到解决方案的借力点。
尽管保供的缺口在整个上海都很明显,但大多数社区并不会像花木这样,由妇联代表政府力量协助居民自治团体去完成商业团购,其中的一大顾虑,是团购涉及到一大笔钱。殷茹媛作为社会组织,了解其中的风险:“你做得好老百姓会觉得你好,你做得有差错怎么办呢?团长那么多,也不是完全能听你的安排的。”
虽然惠姐为街道解了燃眉之急,但仍有一些不满的声音。起初,供应商那边专门安排了90个工人,为花木惠姐团做闭环保供。那个时候大多数团购的蔬菜包可能会卖到60-80元,惠姐的价格是40元,很是畅销。但是单量太大,工作量也跟着暴涨,干了一个月,90个工人辞职到只剩36个。接下来的三单里,开始有蔬菜不新鲜、送货不及时的情况出现,居民的抱怨声渐渐出现,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也直指惠姐是“垄断”,一路举报到市妇联、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志愿者们也开始寻找新的供应商,最终在嘉定的一处农庄找到了更便宜、稳定保供的绿叶菜。一番砍价,绿叶菜以25.8元5斤的价格拿下,农庄还安排了专门的冷链车,每天中午现采,傍晚配送到小区。
到了4月,惠姐又被网暴了。起因是中远集团为花木提供了保供葱,一包5斤8元钱,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一万份。面对还有强大库存的合作伙伴,花木给中远集团写了份感谢信发过去,想加固合作,却流传到网上,被解读成“花木惠姐把中远集团捐赠的葱变卖赚钱”。为此,李碧波还写了一份澄清报告,“想想收到的居民感谢,我最后还是忍了。”
志愿者那边也有急风骤雨。惠姐在最初开启时是公益性质,不允许赚差价,甚至有时候因为平台提现产生手续费,一些志愿者还不得不贴些钱进去。但不免也有人认为,我出了力气,每单赚个几元的辛苦钱也是应该。一些居民发现溢价后无法接受,更多的志愿者以无偿的方式承受着各种可能的抱怨与发难。李碧波说,惠姐推行到半个月的时候,就有几位妈妈打来电话向她哭诉。
“其实我也算过,下面的团长有可能守不好规矩,那我可能也得为此担责。但算来算去,还是应该先想着25万居民张嘴等着,确实吃不上饭了。所以后来,我估了一下底线,就是保证自己不参与一分钱利益。我们团队就上了。最坏都已经想到了,剩下的都是更好了。”李碧波说。
持续织网
社区自主自治程度高,是几位采访对象不约而同提到的点。殷茹媛告诉《中国慈善家》,2014年开始,乐群就在为上海的一些区和街道做楼组长培育工作。每栋楼选出一位楼组长,每个街道再推选一位楼组长代表,到乐群策划的“楼组长联谊会”上培训增能,一月一次。乐群还会为楼组评星,逐渐推行楼组自治标准化建设。
“楼组长是很重要的志愿者,能帮居委会承担很多工作。包括疫情期间,了解各户居民背景、通知组织核酸,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样一来,小区的毛细血管末端就有了一支骨干自治团队,在疫情这种需要以最小单元行动的突发情况里,能够很好地上传下达,直达群众需求。
“像庄文菁的‘联洋妈妈’,也是一个能连接各个小区的组织,每个小区有带头人,就能迅速动员起来。”殷茹媛说,“最初,我们也是想到联洋的自治基础比较好,所以才决定把联洋作为发起点的。”
2020年2月27日,上海,浦东新区花木街道联洋年华小区,智能化机器人“金宝宝”上岗,机器人巡逻员在小区内巡逻,进行在线直播。图/视觉中国
在浦东,乐群还有一个家庭社工项目。每个街道设立一名家庭社工,他们平时会下沉到各个社区和居委,摸排一些危机风险人群,比如有残障、孤儿、重症老人妇女儿童的家庭。社工会入户进行探访、评估需求,以便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精准快速地回应。
家庭社工也在疫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花木在内,社工们共服务了70多名即将生产的产妇。志愿者一方面电话回访安抚情绪,另一方面帮助产妇协调居委会和医院,尽可能及时地赶往医院做产检和护理。
正是这些多年前铺开的探索实践,为“上海团长”和“花木惠姐”的诞生提供了扎实的架构基础。没有这些积累,封控下的多方联动恐怕难以在短时间内搭建起来。李碧波告诉《中国慈善家》,如今疫情保供已经不是首要困难后,她正在考虑将花木惠姐转型为驻地商户和居民团购能够直接对接的平台,做成常驻状态,一方面让居民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东西,另一方面让受重创的商户们快速获得营收。
采访中,庄文菁特别提到,花木街道有一些企业,在疫情期间找到她们,以让利的方式做公益。还有企业专门关注到老人的需求,考虑到一些孤寡老人很难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和团购平台,他们直接找到社工,根据平日积累的家庭信息点对点为这些困难老人送菜,花销由企业全额承担。
花木街道也设有一个社区基金会。遗憾的是,基金会周围仍有不少道道槛槛,还未能像做企业公益那样把钱精准地送到困难户手中。花木街道社区基金会理事长张会告诉《中国慈善家》,基金会成立时由街道与企业出资,启动资金为固定资金,不可挪用。每年,基金会需要额外募集启动资金的8%投入社区项目。
张会坦言,社区基金会作为近些年新落地的组织,如何找到更合适的项目并筹措资金,是主要的难点痛点。花木的社区基金会近年人员多有变动,无专职人员及专业人员,也还未有一间固定的办公室。目前,张会在社区服务中心工作的同时兼管基金会。疫情期间,她也下沉到居委会,住在办公室里做一线工作。基金会能做的事情不多,只在疫情期间对接了一些企业的捐赠需求,把他们提供的抗疫物资下发给居委会。
殷茹媛介绍说,在上海的一些其他街道,也有做得风生水起的社区基金会,“比如浦东的洋泾街道,他们是请专业的社工团队独立管理,秘书长也是专业社工出身。”《中国慈善家》查阅报道发现,洋泾街道社区基金会在疫情期间承担的工作与乐群类似,即培训自主团购的团长、对接困难家庭的需求。
目前,上海民政局官网共有50家注册在案的社区基金会。如何让这些基金会在社区治理中扮演更灵活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许是各社区接下来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目前,花木妇联正在计划把接下来的一些妇女儿童帮扶项目落实到社区基金会,借助他们的审计程序铺开项目,也能引来资金,盘活运营。
今年的“520”,惠姐志愿者们自发做了一次助农团购,一口气买了三四千朵滞销的鲜花,拉到街道里帮忙出售。“20支1束,她们才卖11块钱。那天花木全是鲜花,我们妇联拉了一辆厢式货车,到处发。”想起当时的场景,李碧波笑得很开心。她的办公室里,有不少绿植和花枝齐齐码在窗下;朋友圈里,她也晒出了那天惠姐们捧花的照片。这是一群爱花之人所留下的线索,花与木交织形成一片绿荫和遮挡,让许多人捱过了酷暑和暴雨。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



杂志
2022-08-22

杂志
2022-08-22

杂志
2022-0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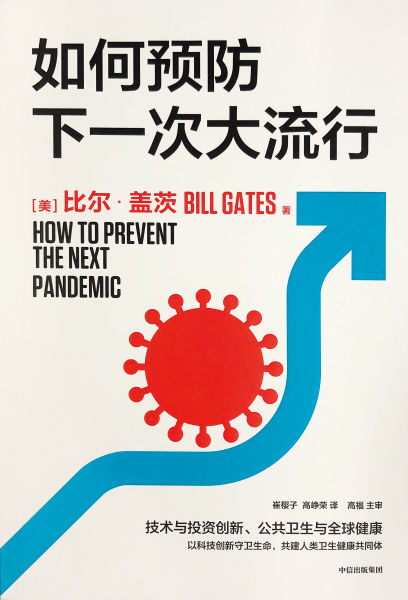
杂志
2022-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