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 · 2024-04-24
中国慈善家 · 2024-04-24

公益对刘小钢来说有过痛楚。在二十多年前,她第一次正经踏足公益,就要面临突如其来的抉择:留下来陪伴癌症晚期、摔倒住进ICU的母亲,还是按时赶去山区的学校,参与奠基捐出的教学楼?
那时候她的选择足以说明一切——尽管无比犹豫和挣扎,她还是飞去了公益一线。
“我总是觉得,我在做我爸妈希望我做的事。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做的事情,他们其实会感到安慰。”她这样告诉《中国慈善家》。
如今,千禾社区基金会理事长刘小钢,已是公益圈里的大姐大。她每日风风火火,与千禾的团队一同深入社区一线,带领着一群居民一同寻找社区乃至社会疑难杂症的解法。解题的乐趣,以及对公共价值观的追求,让她不知疲倦地奔跑了二十年,一刻也不敢耽搁:“钱,你不知道多少是够的;但是命,你是知道的,就这十几年。”
寻找生命的价值
今年69岁的刘小钢,把自己的人生划分成了三个阶段:二十年上学,二十年经商,再二十年则是做公益。她把这第三个二十年选作“生命中最开心的二十年”。理由无他,只因公益是自己心之所向。
曾经,刘小钢是第一批踏着改革开放浪潮,盖起高楼大厦的人。1981年从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刘小钢进入广东省外经贸委调查处工作。但她觉得体制内按部就班的工作逐渐“没了意思”,于是辞了职,下海创业,在香港做起电脑生意,很快闯出一片天地。1994年,刘小钢回到广州,入股房地产开发,一做又是近十年。
在经商这条路上,她无疑是成功的。但那种似乎“被绑在战车上”一直不停转的状态,让刘小钢产生了动摇。2003年,她决定关掉公司,毅然决然、头也不回地踏上公益之路。
那时的她只是个门外汉,连“非营利”如何定义都没完全弄清楚。但冥冥之中,可能是命运的感召,她开始了公益的修炼。

《中国慈善家》:从政府部门任职,到下海做生意,再到现在当全职公益人,这种身份转换难不难?
刘小钢: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都曾问过我。在我看来,我觉得它是特别自然的,没有说生命中间发生了什么巨变,让我去狠下决心什么的。
其实,第一是因为当时的市场环境比较不好,觉得很累,有点厌倦。第二是我自己感觉,我的热情好像有点用完了,很难再对商业提起特别大的兴趣。但是那个时候才40多岁,我就觉得好像我这种人不工作也不行,下半生你总要找一个什么事情做,对吧?你叫我退休,我会很难接受。
于是,当时就反复地问自己,除了现在的事情,我还能做什么?什么东西还能够成为下半生的一种精神寄托?最起码要让自己觉得很开心、很有激情,愿意去投入才行。
那个时候大概是2003年。我当时正在卖楼——我们盖了一栋楼,但特别难卖,也想了N多种办法去卖它,然后慢慢地把最难的时候熬过去了。但是我已经真的觉得很厌倦。
于是我去了英国,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学英文的。当时觉得我要给自己一个时间和空间远离工作,不要再去被工作缠绕,然后思考一下我自己到底想干吗。另外,我当时也想把英文稍微地捡一下,已经离开大学20年了,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选择在那里待三个月。
在2001年之前,我每年也会带着我们公司的员工去福利院、敬老院,献爱心。这种其实以前也做,但是根本不知道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这样做。
2001年的时候,我到广西百色去捐了一栋校舍,捐了50万。那是我第一次参与一个有些规模的、不是简单的献爱心的活动。那几年时间里,每年我都会去学校。学校特别偏远,要从广州坐飞机到南宁,然后再坐汽车,之后再换一辆车,花很多力气才能到达山里。那里大概有两三百个孩子。
那个项目当时给了我特别大的触动。我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孩子,还有这样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而且当时我觉得特别高兴,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就觉得,原来钱是可以有这么大的作用的。
以前,我也非常物质主义,到处购物,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50万或许很多,又可能花不出太大的价值。但是当你把这些资源用在了这些孩子的身上,你会发现,它能让几百个孩子跟外部世界有更紧密的连接,孩子们的眼神都活了。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们心灵的影响是很难估计的。所以,一刹那,它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
那一次之后,几年里我也不断地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带书、带些文具用品。他们也总期盼着我们过来。
后来在英国的那段时间,我就总是在想,已经要进入下半生了,一定要选一件事情去做——这件事情得是让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于是我问我自己,过往的哪一件事情让我有这种感觉。我突然间想起来去百色建校的事情,就觉得在那一刹那,真的有那种找到了生命价值的感觉。
政府的工作我干过了,觉得没意思;商业也干了20年,干够了。为什么我不能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去做公益呢?我觉得我的性格里面是有一种喜欢做社会公共服务的基因的,也不想做着玩,我希望能把它真正做成我的职业,用余生去创造价值。这样,我才觉得找到了一个方向。
但问题是我不懂。业余做一下,是可以的,但让我把它作为职业、很专业地去干这件事,我一无所知。除了它是做好事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我完全不知道。
没关系,我不懂就可以学。原来做商业,我也是不懂的,后来去读MBA了。我下定决心要转行,也刚好在英国认识了一个年轻人。她在美国上学,当时正在剑桥交换,她的爸爸是我的朋友。正好在她的毕业典礼上,我跟她聊起来转行的事,她就告诉我,其实现在这个专业挺火的,叫做非营利管理(Non-profit Management)。我想,非营利就是不赚钱的意思吧,听起来就是我想做的。我转行的时候想做准备,到处去找、想学习,可我也得知道在哪学吧?她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突然又找到了一个路径,我就特别高兴。
那个时候,我本来是定了在英国学习三个月。碰到这个女孩的时候,还剩下大概一个半月,我其实已经报了一个英文班,接下来也要去剑桥上学的。但她一跟我讲,我马上觉得迫不及待,还浪费啥时间啊。
于是我马上跑到剑桥的社区图书馆上网,去找哪个学校有这样的专业。当时我儿子在美国读大学,我也跟他讲了我的想法。他觉得我疯了,说我英文这么臭,20多年前读的英文,现在早都不记得了,还想去美国读大学,根本就不可能!就这样给我泼了一桶冷水。但我觉得只要我愿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总能去争取。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性格,特别倔强。

其实我儿子说归说,他还是给我在美国买了一本书,收录了所有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专业排行榜。我拿到这个东西简直如获至宝,在里面翻到非营利机构管理专业,前十名全是名字如雷贯耳的名校。我胆子很大,报了前十里面的四间学校。我想着,不收我也没关系,我就先去美国读一年英文。我这个人,一旦知道目标在哪里,就会设计一条路径,然后全力以赴,不管结果如何。我直接放弃了剑桥的课程,飞回国内把工作全部安排好,楼也让别人接手去卖。最大的问题是我英文的确不好,托福考试半年的准备时间里,我必须得想办法——于是我报了新东方,成了里面年纪最大的学生。大班还不行,再报私教,疯狂刷题、买磁带来听。最后我的托福分数差不多是卡线过了前十名大学的最低分数线。
非常幸运,三间大学都给了我offer。先是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然后我等了哈佛很久,那也是我最想去的大学。我还记得到北京去参加面试,哈佛的老师就问我,好好地做着企业,为什么转行?我也把社会服务和捐赠的经历、还有我的想法跟他们解释了。我说我很希望用我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回报社会。对方说,你真的感动了我,回去以后,我会在招生委员会里推荐你,希望你能达成你的梦想。
后来我真的收到了哈佛的录取通知——虽然它是有条件的,需要我先去上一个月的语言学校。
那个时候,我根本已经无心卖楼、赚钱了。当时我手上还有一块地,甚至那个地点比我现在盖好楼的地段还要好——是现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我如果坚持把它开发完的话,还可以赚很多钱。但我觉得它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生命有限,相对于我的时间,我觉得那个钱不值。我就完全没有犹豫地把地给了政府。其实我亏了600万,但无所谓了,我觉得我赢得的是时间。那时都快50岁了,再卖楼,我下半辈子可能没有机会了。
后来我想捐钱去推动一个大项目的时候,也后悔过那个决定。如果当时把这块地做了,起码可以多赚一大笔钱,就有钱可捐了。但后来想想,什么事情都是要有交换的,对吧?要拿那笔钱,就要用时间去换,甚至现在还做不做公益,也很难说了,生命的路径可能都会变化。
所以这么一想,我又不后悔了。我能够顺利转行,现在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更重要。没钱就去筹款,总有比你钱多得多的人,得有办法用你的能力去感召别人来支持你的事业。钱,你不知道多少是够的;但是命,你是知道的,就这十几年。
转行了以后,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开心的,就是这20年。这20年,跟我直接有利益相关的事情越来越少,脑子里想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也就不会令你纠结。
一个人纠结,往往是关于个人的事情。但一旦你没有了这些羁绊,你的生活里自己越来越小、别人的事情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就不会再有纠结,只要尽力就好。因此哪怕有很多困难,我实际上都不会觉得它真的难。现在我也觉得自己幸运,感谢上天在20年前让我做了这样一个关键的选择。

《中国慈善家》:虽然你说这是生命中最开心的20年,但这里面也有很多困难的时候。那次在妈妈病重的时候,你最后还是决定去百色做公益,应该也是很困难的选择。
刘小钢:是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刺激很大,很难受。那时我妈妈80多岁,已经患肝癌15年了,她一直咬牙坚持。到了2001年,其实是最后一个春节,她一直在医院里,非常虚弱。我把她从医院里接出来,春节哪里都没去,一直陪着她。
广西百色的公益是陈开枝(时任广州市政协主席)带我去的。2000年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全版的关于他的报道,讲他扶贫、做公益。我父母也是政府公职出身,陈开枝是我的叔叔辈,在大院里看着我长大。我觉得他们这辈人做公共服务,其实潜移默化地对我有不少影响。
后来有一次看戏,在休息室碰到他,我就问他做公益能不能带着我。他评价我是傻妞,觉得从来没人跟他这样讲,他一般都是得求别人支持他。后来,他到六隆镇去的时候,想起了我,把我介绍过去给学校捐楼,我也和他一块儿去那边探访了很多次。
那年大年初三,学校的楼要奠基,我准备第二天一早八点多的飞机去广西。结果当晚我妈起来上洗手间,摔了一跤,我们赶紧叫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忙到四五点钟。
我当时思想斗争特别激烈。再过几个小时本来该去机场了,但我妈又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的特别地挣扎。
大概早上五点多钟,我给陈开枝打了个电话。我说,实在是不能陪你去百色了。他一听,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也很矛盾。但他其实很难,那一年本来有好几个奠基项目,别人都说不能去了,他是寄希望于我的,觉得好歹还有一个人能支持他。可我也说不去了,他就有些绝望。
最终我还是上了飞机。学校活动结束后的那天晚上,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收到病危通知书了,你必须马上赶回来。后来我哥跟我说,妈妈当时一醒来发现我不在,都要气死了。大概我回来十天后,她就走了。
这对我来讲是挺心痛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总是觉得,如果爸妈知道我在做的事情,他们其实会感到安慰的。陈开枝觉得在这件事情他很对不起我。他其实是我很重要的公益引路人。如果当年不是跟着他去做这个项目,我可能也不会有今天,因为这个项目给我的一种触动,以前真的没有过。

望高与俯身
在哈佛学习公益,刘小钢是站在高处的,她很快掌握了“望高”的方法,但回国后,她却发现“俯身”才是更需要去上的一堂课。
在国外,她接触到“社区基金会”的概念,被其理念所吸引。这类基金会把视线集中在一个地域内,其中的人则共同参与构建社区共同体,开展项目来谋求公共利益。人们可以成为捐赠者,可以成为规划者、实践者,也同样能成为受益者。而当作为基本大单元的各个社区进入健康的自我运转状态,整个社会也将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意气风发的刘小钢,希望把这个模式带回中国,但此番栽种却在初期遭遇水土不服的尴尬。家庭环境优渥、无忧无虑的她,在公益中才慢慢领略到人间疾苦,她开始“趴在地上学”,走到基层里和人们打成一片。
2009年,刘小钢与两位朋友一同发起成立了千禾社区基金会——这也是中国第一家以“社区”命名的基金会。经过15年的探索,千禾逐渐聚焦在流动人口与环境保护两个议题上。
其中,流动人口与城中村的聚集,是广东极其突出的社会现象。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广东省内共有超过5206万流动人口,且还在不断增加,人数相比上一个十年周期增长51.71%;其中省外流动人口达2962.21万人,位列全国第一。
外省流入广东的人口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千禾也因此将流动人口问题作为本社区关注的第一重点,针对流动家庭亲子关系改善、流动儿童教育质量提升等问题展开工作。不仅仅是搭建、完善家校社系统从而保障人群权益,刘小钢与千禾更相信,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远非被动者。如若激发出他们的自主能力和活力,他们很快会为自己的社区带来更多改变。
《中国慈善家》:在哈佛读书时,你曾经拍下了和波士顿社区基金会总裁的一顿午餐。当时你们聊了什么?
刘小钢:其实当时国内去哈佛肯尼迪学院读书的人不少,也有很多原来就做公益的。但是我去哈佛上学时对于公益一点都不懂,知识积累全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肯尼迪学院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会在学生范围内做一次拍卖筹款,形式叫做默拍。他们在一间屋子里放了很多不同的拍品,你看中了什么,就在上面写个价格,两个小时之后,价高者得。
拍品很多,项链、耳环,还有各种各样的书之类的。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与波士顿社区基金会总裁吃饭。我心里想,好有意思。因为我本来也是来读这个专业,而且我根本不知道社区基金会是什么,但总之它是基金会,是做公益的。我想近距离接触一下有经验的公益组织领导人,那是我在当时特别需要的。
我直接就写了200美金,志在必得。果不其然,只有我一个人拍了。事实上,那顿饭是总裁请我的,我的钱则捐给了校方。
那时跟他聊了很多。我是个小白,什么都不知道,就从“什么叫社区基金会”开始问起。社区基金会对于社区改变有什么价值,然后是怎么做的,做这个会有什么挑战,所有有关社区基金会的事情,我全部都请教他。
当时我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社会的改变其实是基于每一个社区的改变的,每一个人又都是在生活在社区里面,大到总统,小到扫地的。如果社区里面的人是积极的、是关心公共事务的,社区一定会好。如果说一个个的小社区都健康了,这个社会也一定会好。
我就在想,回来以后,我真的很想做一个社区基金会。其实读书期间,我也深入了解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基金会,到最后我发现最喜欢的还是社区基金会。我很想从最基层的改变开始,慢慢地引发自下而上的变化。可以说,那顿饭也是我想做社区基金会、做千禾的开始。

《中国慈善家》:中美两国差异很大,社区的概念可能都不一样。一开始也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后来是怎么调整的?
刘小钢:我去哈佛学习的目的,是回来做我喜欢的事情,于是分分钟都是在用国外的理论对接我脑海里的中国,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中国的现实是怎么样的,回来以后才发现根本就对接不上。
我形容我当时的状态,是“在飞机上用降落伞跳下来,扑通就挂在树上,上不去,下不来”。当时其实也想过,要不然我就回商业算了。但问了自己100遍,我都还是觉得不愿意回去,我还是想干这个。
后来朱建刚老师跟我说,你现在如果决定做这个事情的话,就得趴在地上学,慢慢地你会找出一些线索,去对接你学的东西。于是我按照老师的意见去认识一些打工的朋友,看他们如何把人组织起来,和一些群体慢慢混熟,我才觉得自己有一些进步。
所以后来朱老师到处跟别人讲,你们别说刘小钢不行,她现在比我们还更加了解草根组织。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正好是广东狮子会的会长,带着会员志愿者们到汶川去救灾,又认识了很多当地的草根组织,也慢慢感受到公益氛围有了变化。
我觉得一个好的社会,每个成员需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有选择的意识。自己要基于自愿,投入到一些公共事务里。
欧美社会的情况,跟他们的宗教历史有很大关系,服务社会作为教义的延伸,成了他们很普遍的观念。而在中国,有时大家很依赖政府来替自己做好一切,对公共的事情不愿意负起自己的责任。
做社区基金会的价值恰恰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把社区里普通人的自我意识,通过参与各种活动,把它激发出来。所以千禾工作的出发点就是在人身上,如何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让大家相互看见、相互关心,从而在乎自己生活的社区。这样一来,社区可能就有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千禾成立十五年来,我们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其实过程非常曲折,也转变了不同的路径和做法,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基本的价值观——以人为本的社区。促使人的变化,才能让社区变化,而不是只简单地去做各种活动,把社区搞得热热闹闹而已。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很慢但又有韧性的社区发展模式,或许在十年后会看到变化,也有可能会是失败的结果,但我觉得都没关系。
《中国慈善家》:筹款情况如何,资金上有没有困难?
刘小钢:还可以。2022年大概是1500万,去年是2000万。但现在我觉得要更加注重筹款质量,不是说有人给你钱、叫你干吗,你都去做。
以前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为了筹款,就真是这样。但筹款的目的是什么?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为了它找人、发展新议题,等于被钱牵着走。
我们现在比较笃定,知道工作的战场就是在社区,想在这里深耕,把它做好。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捐款人,在理解我做的事情后,能不计较短期效益地支持我们。
比如乐高,一直跟我们合作得很好。一开始他们给的钱也很少,但现在已经准备跟我们敲定一个长期的合同了。他们发现自己的产品和社区的场景很契合,把乐高玩具发给社区的流动儿童们,他们可以通过搭积木去开发想象力、去尝试创新,从而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今年努力的方向,也会是像这样提高善款的质量,更有效地对接社区的需求,共同去引发一些变化。

《中国慈善家》:千禾一开始的定位是资助型基金会,这些年也经历了许多调整,这些调整背后的思路是什么?
刘小钢:其实千禾发展到今天,真的是换了很多不一样的做法。我们最初是支持草根组织,看到哪个做的事情和我们价值观一致,我们就给它支持,大概有几百个组织。后来有很多慢慢地也没了。
这个做法不能说错,但是好像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感觉沉不到底。像我们这样的资助型基金会,需要去筹款,但捐赠人不明白,你做公益就去做公益,为什么还把这个钱给一个别的组织?所以我们筹款也非常困难,而且资助到最后,好像也不见得非常有效。
所以千禾的这15年,其实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慢慢发现,我们是一个很小的机构,资源非常有限。这么小的基金会,如果想涉及各种各样不同的议题,到最后就是一无所获。
我们发现,必须要聚焦。但怎么聚焦?我们想到,第一,千禾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基金会,是广东省注册的基金会。第二,我们地域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就是流动人口问题。广东省是全中国最大的流动人口省份,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议题,就是流动人口。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最后一公里”的基金会。很多头部的基金会,它不需要去向外筹款,可以做一些统筹的、提升行业发展的事。而我们虽然资源不算多,但对地面是最了解的。于是,我们就把焦点确定在珠三角的流动人口议题上。
现在这也是我们很鲜明的标签。再去筹款时,一讲对方就清楚了。他会看到我们在这个议题里的能力,比如很清晰地了解到有多少组织在做同样的议题,这个议题里面有哪些重点,我们给出的解决问题的路径是什么,怎么样让关注的群体发生变化等等。我们的定位越来越明确,资源筹集能力也越来越强,积累的经验和能力也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和一线草根组织一起成长的资助型基金会——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
女性不止半边天
千禾社区基金会的办公楼坐落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小巷子里,那是一栋三层的矮楼房,空间有些局促,刘小钢作为理事长更是没有给自己留一个单独的办公室。站在办公室里往外望去,举目一片高矮错落的小房子,老城区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无论是办公室内外,刘小钢总是和大家能打成一片,似乎走到哪里,她身边总是围着许多人,颇有一种一呼百应的领袖气质。
《中国慈善家》:我们这一期杂志的封面报道聚焦女性公益领袖,对于自己的女性身份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刘小钢:我真的基本没有性别意识,好像是“雌雄同体”。这可能跟我家的情况有关。我妈是一个非常好强的女生,文化程度不高,但还是特别喜欢学习。结婚之后,我爸也留给她很多空间,她就去党校、去各种课上学习。我们家也比较少性别上的区分。我一直是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所以原来谁要是问我关于性别的问题,其实我是没有话讲,没有这个意识。
但是自从进入社区之后,我发现性别的分野的确是有的。在我们的社区里,其实管孩子的一般都是妈妈。我们搞了很多的社区活动,爸爸都不出席,基本上都是妈妈。而且我发现,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妈妈改变,家庭就会改变。
我越来越感觉到,如果我们讲社区话题,妈妈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支持过一个打工一族的社区,其中一个打工妈妈在我们的支持下出来做了一个公益空间。她身边有一批妈妈,原来只知道在工厂里打工赚钱,每天生活很枯燥单一,但是慢慢地把她们组织起来之后,她们的活力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她们去读了千禾开办的关于孩子的各类课程,成为了城市支教的志愿者。这个打工妈妈

的群体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也给她们自己的家庭带来很好的变化,这让我觉得妈妈的力量真的非常大。
当然,我们要想办法把爸爸再拉进来。但是妈妈的改变,绝对是关键的第一步。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社区工作的机构,对于女性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慈善家》:你觉得女性从事公益有什么特别之处?
刘小钢:在我们公益领域,从业者大概60%都是女性。女性在这个领域里绝对不止半边天,一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非常大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觉得公益行业,相比于商业或政府来说,对女性是比较友好的。不过,在有资源的那一端,好像女性也不是很多。可能是在商业或者政府方面,留给女性发展的机会还是不够多,所以掌握资源、顺势进入公益领域的比例也会小一些。而在草根民间组织、民间社会服务机构这一端,一线的领导人还真是有很多女性。
公益领域跟别的领域最不一样的特点是,每一个人的自主性其实都是很强的。如果不是有极强的自主性的话,他不一定会选择进入这个领域。要赚钱,可以去企业,要当官,可以去政府。之所以选择公益行业,很多人是基于一种价值的选择,而这种价值的选择应该是一种非常自主的选择,不是“不得不为之”。所以我觉得,选择做公益的女性,一定真的是有思考过的。
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女性来说,她真的可以尝试去看到一种可能性。不是说只能去给人打工,如果对哪一个社会议题感兴趣,其实你完全可以自己去尝试带领一个团队去做。
《中国慈善家》:家人如何看待你的公益事业?
刘小钢:我觉得我跟儿子都是比较独立的两个人,他不会过多谈论我做的事情。比如去年年底我获得了爱心奖,我就问我儿子和儿媳,你妈很奇怪地得了一个奖,有没有兴趣去参加一下颁奖仪式?他们去了,之后也点评了一下,给了我一点认可。
有一点让我觉得比较开心,那就是我跟我儿子在价值观上有很高的共识。对于我做的事情,以及平时对于新闻时政的讨论,我们很多基本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
当然,我们是两辈人,所以我关注的人群不一定是他关心的。但是他对一些公共事务有他的理解和角度。比如他对宠物非常有感情,他觉得猫狗是不能买卖的,如果喜欢就得去领养。如果拿它当一个商品去买卖,就绝对触及他根本的价值观,他会非常愤慨。
他现在还在创业。如果有一天,他也有兴趣做公益的话,我希望能支持他,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公共议题。
《中国慈善家》:现在回望自己走过的商业和公益道路,你如果回到从前,会从一开始就选择做公益而不是商业吗?
刘小钢:我觉得两个领域之间,很多逻辑是通的。当然,公益机构会考虑弱势优先,会把资源都用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商业也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但它是用产品、用商业的逻辑为社会作贡献。我觉得两者要达成的终极愿望,都应该是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它们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我越来越觉得,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企业,你本身一定是要带有公益目的的。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用于给股东产生最大化的效益,这可能真的走不远。
如果放眼世界,你会发现,好的企业一定是受人尊敬的企业。受人尊敬,源自于它的可持续发展导向,它的公共目的和它的产品已经不能分割了。为了赚钱造假或者什么黑心企业,根本不会再有生存的空间。企业必须慢慢发展出社会责任感,你做的产品,如果希望它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它内在的逻辑必须指向公共目的。
我以前不懂这些。但今天如果我再回去做企业,我觉得自己会做得更好。而且我的企业一定是一个向善的企业,毕竟,我好歹干了20年的公益嘛。
作者:龚怡洁
图片:陈骥旻、受访者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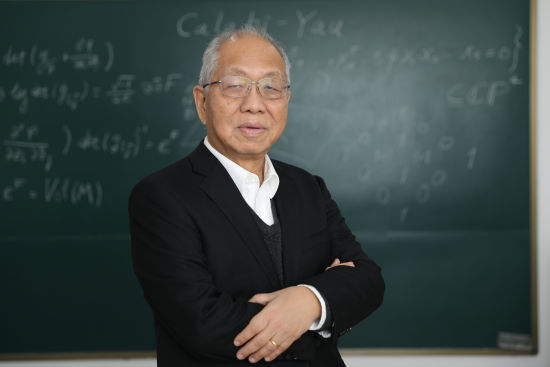
公益人
2024-04-24

公益人
2024-04-24

公益人
2024-04-24

公益人
2024-04-24